
我是在四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确诊患上“旋转视野症”的。医生看着我,我看着医生,她的脸以鼻尖为中心旋转起来,最后变成了一串同心圆。鼻尖是粉红色的,有若有若无的汗珠发亮,形成中心的亮点。嘴唇的颜色更红,与眼睛的深棕色、眉毛和睫毛的黑色混合在一起,快速地闪动着。在亮点和黑红色闪动的圆圈之间是小行星带一样的浅棕色雀斑。
“你的雀斑很好看。”我试图奉承她一句。 她的脸颊是比鼻尖更红,但比嘴唇颜色略浅的微妙颜色,这种颜色显得面积很大,也许是因为脸红了。
旋转视野症和其他很多毛病一样,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治疗的方法。患者一般会在随机情况下发病,发病和好转的机制至今仍不清楚,而治愈的方法和其他很多毛病一样都是谜。
事实上,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幸运的。毕竟如果你一定会得一种怪病,那么视野旋转症肯定不是最糟的。除了不能开车和从事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工作以外,这不会太影响人的生活——我是一个作家,如果发现视野突然开始旋转最后变成一组同心圆,我只要暂时放下无法看清的纸笔,或者闭上眼睛用电脑键盘盲打写作就行了。
当然,这个疾病一开始还是挺令人头疼的。我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惊恐万状,因为眼前的一切都在飞速旋转,直到变成了一圈一圈的波纹。但现在我已经习惯它每一天发作十五次,我甚至会乘着发病时间仔细欣赏原来熟视无睹的景色,它往往能给写作带来灵感。这种旋转的视野很像长时间曝光的星空,它甚至能将所有的丑陋拖长成一条线,只留下美好的几何图形。
照理说,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,我找医生的用处微乎其微。但医生能够为我开一张相关的证明,这对我领取疾病补助很有帮助。同时,视野旋转症相对少见,医生可以将我作为病例研究,这种研究能给我带来一小笔补贴,也给我能够缓解症状的期待。顺便,医生长得也很漂亮,无论是欣赏她的笑脸,还是猜测哪一圈是她的哪个脸部器官,都很有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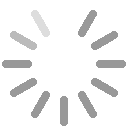
医生站起身来,抓住我的手。她的力气很大,比任何一个我见过的男人都大。她拽着我旋转起来,我的视野在平面旋转的基础上变成了立体旋转。虽然我已经适应了视野旋转的毛病,但双重旋转还是让我惊恐,我仿佛失去了支撑在地面的双腿,整个人惊悸地抽搐起来,以至于将医生的手也握得很紧。
这是医生的疾病,不定期发作的“随机抓人跳舞症”。
我轻易地原谅了医生。这是必须做的事情。否则,别人也不会在我突然停留在路中间,像个睁眼瞎子一样迷茫的时候原谅我。疾病就是疾病。你总得原谅人的疾病。尤其是这种不治之症。
每个人都有一种不治之症,也仅有一种。在这个世界上,这件事情就好像开车加油要钱和人都会死一样确定。我的不治之症是视野旋转,医生的不治之症是随机抓着人跳舞。这就好像是我们的身份证一样确认无疑。
总体来说,我们的病只会恶化下去。到最后,我多数时间都会在旋转的视野中度过,而医生则会见人就跳舞。考虑到她是个漂亮姑娘,这好像算不上太大的麻烦。但这世界上的麻烦要说小,都大不到哪里去。我可以用一种在中心有一个轴承,可以竖着旋转的托盘,把我要读的东西放在托盘上,让它与我的视野同步旋转。
我也会在家里尽可能布置同心圆状的东西。无论我的视野是否旋转,它们看上去总是一样的,这能给我一些安慰。
确诊后的第六个月,我的病情已经发展到每天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处在视野旋转中,而且发作的时间不定。医生的病情也发展到了新的阶段——她依然抓着人跳舞,但是力气更大了,而且会把人在空中抡着转圈。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倒是不错:只要让我的视野旋转与她将我在空中抡圈子的角速度保持一致,我就能够看清楚东西,尽管头挺晕的。
我个人认为,如果我们俩的病最后都发展到末期的话,我们将会成为一对优秀的情侣——我们俩形影不离,我的眼睛可以看清东西,她也总有个人可抓。到时候,我们就会像一台风车一样在这座城市里到处行走。
我曾经说过,我的家里有好多同心圆状的东西。我的门把手外面画着一圈同心圆,用红、蓝、黑、白蓝五种颜色的排列作为标记。这让我不至于在家门口还找不到家门。我的沙发则能够为我提供一个确定的锚点,只要盯着中间的红点看,我就能确定它的方向,摸索着坐到上面。在一切动荡不明之时,只有它是安全的。

[完]
[设计师 Richard Hutten 设计的“云”羊毛椅 Layers Cloud Chair,从里到外全部用 Divina 羊毛,逐层叠加叠了545层,非常非常非常重,200 多公斤的份量让任何坐着它的人都会显得轻盈。顺便,做这个椅子花了600个工时,简直相当于你在家拼装一张宜家椅子的时间了。来源:core77 ]

